
多年来,我一直认为玛西,那个戴着眼镜、痴迷于书本的女孩 花生 ,是亚裔美国人。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多么希望亚裔美国人出现在我最喜欢的漫画中;这是关于我对她的认同程度。通过玛西的各种故事情节,查尔斯·舒尔茨描绘了一个害羞的人通过达到极限而认识到自我价值的挣扎。
我之所以相信玛西是亚裔美国人,部分原因在于她刻意的不伦不类的描述。舒尔茨从未给过玛西的姓氏,这使得她的种族背景变得模糊。她的深色头发在报纸上被涂成了黑色。她那副厚厚的不透明眼镜遮住了她的眼睛,让我只能想象它们的形状。也许舒尔茨想要一个读者可以将自己投射到其中的角色。又或者,这可能是个性匹配的一个例子。玛西认为自己平平无奇,这一点也延伸到了她的外表上。
Marcie 于 1971 年出道,当时正值乐队转型时期 花生 。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,大部分 花生 每日连环画都是独立的故事,只有几条弧线,最多持续一两周。但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,舒尔茨让这些叙事持续了三到六周,人物形象也更加丰富。
这些较长叙述的最大接受者是 薄荷帕蒂,一位崭露头角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 谁反抗性别角色。在 70 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薄荷帕蒂的知名度几乎与查理·布朗相当。正因为如此,玛西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其中。她是薄荷帕蒂最亲密的知己和最好的朋友,但很多时候,她也可能是薄荷帕蒂的影子。
薄荷帕蒂在玛西的带领下声名鹊起,这给了舒尔茨时间来发展玛西的性格。她最明显的性格特征是她的自我怀疑。她很少考虑自己,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安抚他人上。
玛西几乎总是出现在有计划的活动中,例如夏令营或学校。薄荷帕蒂不得不敲她的门让她参与一些事情,但很多时候,玛西不能出来玩。她必须练习她的管风琴。她必须学习。她必须读书。玛西的日子里几乎没有闲暇时间。她的父母很保护她,他们保护她安全的方法也让她很忙。
当然,这种不平衡对孩子的影响是,孩子变得不平衡——大脑发育过度,但生活技能和社交能力发育不足。糟糕的自我形象也随之而来。当社交活动被如此公开地阻止时,很难想象它会令人向往。玛西承认自己缺乏吸引力,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与某人约会的行为似乎很抽象,就像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的事情(如果有的话)。
与玛西的父母类似,我的第一代父母也担心他们的家庭结构之外的危险。当我长大后,我的父母仍然密切关注着我——我直到上大学才约会。朋友很少,社交技能也较少,这让我对我那微薄的熟人表现出卑鄙的忠诚。我是一个拼命讨好别人的人,但现在回想起来,我的方式很尴尬。每当玛西称薄荷帕蒂为“先生”时,我都会感到畏缩——我知道那种不称职的感觉,我尊敬我的朋友,而不是把他们视为与我平等的人。
我花了时间,逐渐建立了信心,才知道我的熟人会因为我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更加尊重我,而不是更少。玛西的故事情节通常围绕这一发现展开。通过她较长的弧线,她了解到维护自我价值和身份的价值,无论是通过维护别人、维护自己,还是只是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。
玛西总是知道该做什么或该说什么;这只是一个失去勇气去做或说的问题。至于能不能做到,以及如何做到,则视个人情况而定。有时,她会情绪崩溃,情绪崩溃。
有时,她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,忍受人们对她说真话的抵触情绪。
有时,她无法坚持自己的主张,从而避免了一场不舒服的谈话。在一个为期数周的故事情节中,玛西缝制了一件滑冰裙——尽管她不知道如何缝制——因为薄荷帕蒂威逼她这样做。
这对薄荷帕蒂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困境,但对玛西来说更是一个痛苦的困境。她让人感觉自己是隐形的;她被忽视,然后因允许自己被忽视而受到斥责。她甚至知道帕蒂没有听她说话,但她还是按照要求做了。
对于他们俩来说幸运的是,情况最终得到了解决。舒尔茨对薄荷帕蒂和玛西情有独钟,他时不时地让这两个可怜的女孩休息一下。但请注意,玛西从未断言薄荷帕蒂是错误的或自私的。相反,她把责任归咎于自己;这是自尊心低的人可能会采用的解决方案。薄荷帕蒂和玛西的友谊得到了恢复,但仍然不平等。他们的沟通问题必然会再次出现。
体育运动也许是玛西最受挫的地方,但这也是她发挥自己优势的地方。用她自己的话说,玛西参加运动只是因为她不想“冒冒犯”薄荷帕蒂的风险。同样,这就是一个自尊心低的人的思维方式——对她的朋友设置限制会损害他们的关系,而不是让关系变得更健康。
有时,玛西会通过消极的攻击行为来表达她的不满。如果她因为玩游戏而感到内疚,那么她就会在这个过程中破坏其他人的乐趣。
玛西有成为一个真正的聪明人的隐藏能力,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。她以“帮助”为幌子巧妙地削弱了薄荷帕蒂,也许是在合理化自己,如果她足够痛苦,就永远不会被要求回来。当然,这一切都比简单地说“不”并坚持下去更好。然而玛西却没有信心如此直白地挑战她的朋友。
玛西最直接的主张发生在体育背景下。当蒂博以性别歧视为由抗议她的参与时,玛西展示了她的直接性。
这一刻我很同情玛西。她在这里玩着她讨厌玩的游戏,试图安抚她不想冒犯的朋友。最重要的是,她还必须捍卫自己在那里的权利?最终,蒂博的辱骂达到了临界点,玛西捍卫自己人性的需要超过了取悦朋友的需要。
最后的那段戏令人兴奋又鼓舞人心。这是玛西我们很少看到的一面,很高兴知道它的存在。在某种程度上,玛西可能会被逼得太远,她会坚持自己的自我价值,而不是屈服。
没有人能够完美地处理所有情况。在整个 70 年代,玛西对被踩踏的反应多种多样,从大胆到被动。就好像她在最终确定一个身份之前尝试了不同的身份。
但经过最初的实验,玛西找到了一种让她与薄荷帕蒂的友谊更加平等的方法。从 1984 年开始,她说服薄荷帕蒂陪她参加古典音乐会,作为她参加体育运动的明显权衡。在这个舞台上,玛西可以感到一切尽在掌握,而她的同龄人则面临着做出失败的风险。 失礼 而不是她。
薄荷帕蒂不由自主地喜欢这些音乐会,这对玛西来说是一场绝对的胜利。在一个罕见的时刻,她可以让某人进入她的世界,并因为这样做而感到被认可。她最终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了友谊。
没有 花生 剥夺比这更多的生活肯定或振奋。对于那些在自信和自我形象中挣扎的人来说,友谊——真正的、原始的友谊——可能会很困难。感觉自己足够优秀并被平等对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但为了这样的时刻,这是值得的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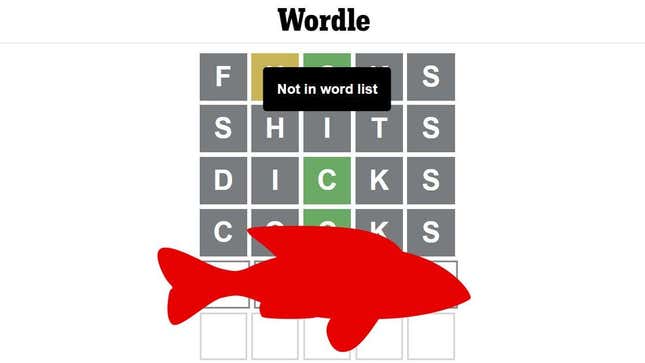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留言